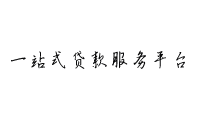「经济发展」余永定:应坚定实行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
发布日期:2025-03-15 09:36:15 浏览次数:
余永定:应坚定实行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
经济发展
★ ★★★★
宏观经济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之间的最佳组合。通胀率和GDP增速两者持续下跌(或持续低于目标水平)本应足以使决策者作出宏观经济处于有效需求不足状态的判断,并采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以刺激有效需求。但由于许多行业存在严重产能过剩,消灭“过剩产能”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应该明确区分在宏观和产业两个不同层面上的“产能过剩”。在宏观层面“产能过剩” 就是有效需求不足。物价指数的变化则是判断宏观经济处于有效需求不足抑或经济过热状态的主要指示器。通胀率低于目标水平,就实行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反之,就实行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产业层面的“产能过剩” 不应该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与节奏。产业(产品)层面的“产能不足”和“产能过剩”是不断变化的,“夕阳产业”可能焕发青春,某个 “朝阳产业”可能会突然被发现仅仅是一个 “泡沫”。政府难以判断产业层面的动态供求均衡水平,产业层面的“产能过剩”问题应该主要交由市场和企业家解决。
一、在宏观层面,“产能过剩”和 “总(有效)需求不足”是等价概念
在宏观经济层面只存在两种情况:第一,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经济过热)。经过一段时间的滞后,通胀将会恶化。政府应该择机紧缩财政和货币政策,抑制总需求以防止通胀形势恶化。第二,有效需求不足。通货膨胀率低于根据经验和共识所确定的目标水平或跌破目标水平之后依然持续下跌。一般情况下,GDP增速也会持续下跌,而且往往会先于通胀率的下跌而下跌。在分析实际经济问题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外部冲击(如疫情),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也会出现供不应求缺口,从而导致通货膨胀恶化。但经验证明:对于供给冲击,宏观经济政策的效用是有限的。如果出现有利的外部冲击,如某种技术革命突然出现,通胀率会下降,但GDP增速应该会提高。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产能过剩,则决策者可能需要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以便使经济增长充分享受技术进步的红利。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无论是源于供给冲击还是需求冲击,供大于求的出现都伴随物价水平的下降。第二,宏观调控当局的政策反应都应是增加有效需求,在不导致物价形势恶化的同时提高均衡产出水平,或使产出恢复到原来的较高均衡水平。第三,宏观经济政策是需求管理政策,只能影响当期有效需求,而无法影响当期总供给(移动总供给曲线),但可以影响未来总供给。
二、“供求缺口”与通胀间的时滞使决策者难以把握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与节奏
通货膨胀率是“总供给—总需求”缺口的函数。出现供不应求缺口时,即经济处于过热状态时,物价上升(或通胀率上升)。反之,物价下降(或通胀率下降)。宏观经济政策是建立在经济增速(给定潜在经济增速)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取舍关系(trade-off)这一假设基础之上的。为了实现给定经济增速目标,可能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牺牲物价稳定目标。反之亦然。如果通胀率超过预设目标,货币当局就会采取紧缩政策。反之则反。对于决策者而言,例如对于货币当局而言,困难之处在于难以预判实行何种紧缩程度的货币政策可以在何时实现通胀目标。换言之,由于“供—需”缺口变化和通胀率变化之间存在时滞,以及增长和通胀之间取舍关系的不确定性,货币当局难以判断为了实现某一通胀目标,当期所实行的货币政策是否会导致经济增速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明显下降甚至硬着陆。反之,货币当局也难以判断为了实现经济增速目标和降低失业率,当期所实行的货币政策是否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导致通胀最终失去控制。财政当局在执行财政政策时,也存在相似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从未经历过高通胀、低增长(负增长)的“滞涨”局面。但自1990年到2012年中国经历过几次比较明显的经济过热(高增长+高通胀)和经济过冷(低增长+通缩)的波动(习惯上称为“周期性”变化)。在这一时期,我们得出三条主要经验。第一,当经济增速已经超过潜在经济增速之时,通胀率可能还处于较低水平。例如,上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高峰出现于1992年。当时GDP增速为14.2%,但通胀率仅为6.4%。决策者并未及时实行紧缩政策,结果通货膨胀在1994年险些失控。如果当年实行紧缩政策早一些,经济运行可能就会更平稳些,调控代价就少一些。第二,当经济已经恢复平衡或已经出现供大于求缺口时,通货膨胀率可能还未下降到位。例如,1996年通货膨胀率已经从1994年的峰值24.7%迅速下降,但仍高达8.6%。政府对进一步降息十分谨慎,直到当年8月才第二次降息。如果当年降息早一些、频度高一些,1998年中国经济增速就可能不至于跌破8%,并在当年陷入通货收缩(外部冲击也是重要原因)。第三,如果通货膨胀率已超过目标水平,但经济依然维持主要是投资驱动的高速增长,政府就不必过于担心未来通胀失控而急于采取紧缩政策。2003年经济出现过热迹象。例如,当年房地产市场异常火爆。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30.3%。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5.77%。商品房销售金额同比增长31.9%。2006年中国GDP增速达到12.7%,但CPI通货膨胀率却由2004年9月的最高值5.2%下降到了2006年12月的2.8%。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2003—2004年的大量投资使2006年的产能得到大幅度提升。虽然总需求高速增长,但总供给也已相应增加。因而,2006年并未出现严重的供不应求状况,通货膨胀率不升反降。
三、要区别宏观层面和产业层面的“产能过剩”
自2010年以来中国GDP基本上是逐季度下降。自2012年3月以来中国PPI在大部分时间是负增长。2012年5月中国CPI增速跌破3%(并在此后近10年中一直徘徊在2%左右)。按道理,当经济处于增速持续下跌、通缩或准通缩(PPI负增长、CPI增速破3%)状态时,政府应当实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以刺激有效需求,使GDP实现同“潜在经济增速”相符的增长速度。但是,由于很多部门都出现了产能过剩(产能利用率低),流行观点认为政府应该拒绝“刺激性”政策,坚持实行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是中性或中性偏紧的宏观经济政策。当期产能是前期要素投入决定的(不排除当期出现外部冲击),因而产能是给定的或决策者无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加以影响的,可变的只有总需求。因而,在宏观层面“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是同一个概念的两种不同表述方式(供大于求=求小于供)。即便产业层面普遍出现产能过剩,也不会改变在宏观层面“产能过剩”和总需求不足是等价概念的事实。假设基年经济整体处于供求平衡状态,各产业的供求关系也处于平衡状态。再假设第二年各个产业和总产能等比增加,同时需求结构没有发生变化,但由于某种原因,总需求增速低于总产能的增速。这样,宏观层面的“产能过剩”是产业层面产能过剩的加总。但这种情况并不改变在宏观层面总需求不足的事实。因为从效用和福利的角度看,公众应该充分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实现经济福祉的提高。既然产能已经提高,除非需求结构已经变化,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刺激有效需求、提高经济增速,使需求适应产能,而非消灭“过剩产能”。事实上,中国多年来的“准通缩”的状况主要是当期有效需求不足而非前期投资过度造成的。如果问题出在前期投资过度,在通胀率迅速下降、出现通缩征兆之前,经济增速应该是上升而不是下降的。中国经济增速自2010年之后就开始持续下跌,从10.6%跌到2012年的7.8%、2015年的7%、2019年的6.1%到去年底的5.2%。通胀率和经济增速双跌充分说明,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是总需求(有效需求)不足,而不是前期投资过度导致的“产能过剩”。针对前期某些行业投资过度导致当期产能结构失衡(如房地产业扩张过度)的情况,在维持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和让市场充分发挥调节作用的同时,政府还需通过其他政策影响当期的需求结构(如对住房的需求),以推动未来产能结构的合理化。
四、宏观经济政策不应以“去产能”为目标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2009年第一季度GDP增速仅为6.1%,CPI和PPI都进入负增长区间。为了抵消这种冲击,2009年中国政府引入“四万亿元财政刺激计划”。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目的是通过刺激投资需求,特别是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弥补外需减少造成的总需求不足。中国政府在2011年3月的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当年的主要任务是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4%以下。抑制通胀和房价上升成为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2011年财政赤字对GDP比和新增信贷锐减导致投资增速锐减。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由年初的13.4%下降到年底的6.5%;同期房地产投资增速由33%下降到28%。如果说2009年“四万亿元财政刺激计划” 是猛踩油门(财政预算由2008年的基本平衡变成财政赤字率2.8%;新增信贷由2008年的4.9万亿元猛增到9.6万亿),2011年则是急刹车(财政赤字率降到1.1%;新增信贷降到7.5万亿元)。在这种情况下,2012年总供给与总需求出现巨大供大于求缺口是难以避免的。可以设想,即便2011年政府并未执行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由于四万亿刺激下的新增产能的相继形成,2012年通货膨胀压力也会下降。这种情况应该同经过2003年大规模投资之后的2006年相似。如果2011年中国政府不采取以抑制通胀为主要目标的紧缩政策,或者像2004—2005年那样,紧缩力度缓和一些,或许2012年GDP增速和通货膨胀率的下降就可以更为温和一些。面对众多行业产能过剩和宏观层面总需求不足的局面,2012年政府虽然提出“扩大内需……是今年(2012年)工作的重点”,但仍然强调“调整政策力度,适时退出刺激政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可见,这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和“刺激政策”(或扩张政策)相对立的宏观经济政策,充其量是指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作为退出“刺激政策”的具体表现之一,2012年财政赤字率略高于执行紧缩政策的2011年,但仍保持1.5%的低水平;新增信贷8.2万亿元,高于2011年,但明显低于2009年。201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2012年PPI的负增长只字未提,只是表示2012年在货币政策运用上,始终注意把握稳增长、控物价和防风险之间的平衡。2013年政府继续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其实,充其量是实施中性的财政货币政策。2013年GDP增速目标为7.5%,低于2012年的实际增速7.7%。2013年尽管“经济持续下行”,但政府依然坚持“不采取短期刺激措施,不扩大赤字,不超发货币,而是增加有效供给,释放潜在需求”“保持总量政策稳定”。2013年本应该是转变市场预期的一年。但是,可能是由于住房价格指数飙升,政府并未在2013年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以巩固2012年第四季度以来经济反弹的态势。2013年GDP增速为7.7%,明显低于年初的市场预期。应该承认,在2011年和2012年,决定中国应该执行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不容易。2013年的情况也是如此。现在来看,如果当时能把通货膨胀率锚定在某个水平,如3%—4%,做为宏观经济目标。如果当时政府针对通货膨胀率的下降,特别是PPI的持续负增长,而不是针对产能过剩的状况,实行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中国后来的增长情况可能会好许多。从2012年以来的宏观调控中我们可以有以下认识:第一,区别宏观层面和产业层面的“产能过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宏观层面,产能过剩等于总需求不足,其表现是通胀率过低甚至负增长和经济增速的下降。总需求不足和产业层面的产能过剩完全可以同时并存。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即便出现相当普遍的产业层面上的产能过剩,政府也应该执行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而不应该把消灭过剩产能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目标,遑论最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第二,作为刺激政策,应该主要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对于其他类型的投资,政府应该尽量减少干预。基础设施是公共产品,无论情况如何,无论时间早晚总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总是能够改善民众福祉的。在需求不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和物价增速过低的情况下,基础设施投资可以产生“挤入效应”,带动由市场和企业自主决定的投资。政府之所以在刺激经济增长时主要是刺激基础设施投资而不是一般投资,正是因为同其他类型的投资相比,基础设施投资在弥补有效需求不足的同时,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因政府的误判导致产业结构的恶化。第三,在产业层面,产能过剩和产能不足(出现瓶颈)是普遍存在和经常发生的。供求均衡的恢复主要靠市场的价格机制实现。对于已经成为既成事实的“过剩产能”,必须主要依靠市场价格机制和企业家的主观能动性来解决。钢铁行业产能利用率低下,价格和利润暴跌正好说明市场机制在发挥调节作用。2012年钢铁行业产能过剩严重,利润率0.04%,两吨钢的利润“不够买一根冰棍”。面对这种形势,钢铁企业自己会采取应对措施。只要地方政府不提供违反市场规律的激励措施,无需中央政府实施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假以时日,钢铁产能应该会自行调整,从而实现钢铁市场的供求均衡。不仅如此,宽松的宏观经济形势还可以减少企业进行结构调整消除过剩产能的成本。第四,对基础设施概念的理解应该更为宽泛。基础设施不仅仅意味着“铁、公、机”,不仅仅意味着“新基建”,它越来越多的涵盖了在公共卫生、养老、教育、体育、文娱等民生领域的投资。我们平常所说的基础设施投资也包含了公共投资的含义。
五、实行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同结构改革并无矛盾
在讨论短期或长期经济增长问题时,为了方便,经济学家往往把问题分为两大类:结构改革(structural reform)和宏观需求管理(或调控)。凡无法用宏观经济政策解决的(增长)问题就称之为结构问题。而为解决结构问题进行的改革则称之为结构改革。结构改革和宏观调控是两个领域的不同问题,解决两个领域中的问题有各自的政策工具。宏观经济政策无法解决结构问题。反之亦然。结构改革和宏观需求管理相辅相成,并不相互排斥。例如,为了增加消费需求,除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手段,如减税,还需完善社保体系,如提高财政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城市低保受益人的覆盖面,并显著提高受益人的受益金额。而这些措施也恰恰是结构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另一方面,在全面贯彻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也并不妨碍实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防止经济硬着陆。现实经济增速低于潜在经济增速本身就是对资源的巨大浪费。仅通过“关、停、并、转”和“去产能”不一定能够稳定物价。即便物价稳定了,如果没有新的增长引擎,经济增长速度也不会回升。相反,在“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通缩”和“债务—通缩”两种恶性循环的作用下,经济增长可能会持续下降,而无法稳定在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上。
六、2024年应实行更具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争取实现较高的GDP增速目标
202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 “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2023年政府经济工作报告明确“有效需求不足”是“突出矛盾”。中央的这种判断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如何正确把握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力度与节奏,将是2024年最后一个季度,中国宏观调控政策面临的最大挑战。一方面,政府应该加快行动步伐,执行更为积极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另一方面,由于时间所剩无多,政府也不应在未做好必须的铺垫之前仓促上阵。应该看到,力争实现较高经济增速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增长是硬道理,没有经济增长,其他一切问题都难以解决。除经济增长之外,中国经济还受到地方债和房地产开发债的困扰。解决债务问题是重要的,但不应干扰经济增长。有观点认为,地方政府在疫情期间对企业的欠债,应由中央政府偿还。这种观点是非常合理的。另外,多年以来中央财政对地方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支持比例过低,地方政府的负债中有相当部分应该是由中央政府承担的。在化债过程中,中央财政应该肩负更大的职责。如果到目前为止政府还没有准备好基础设施投资项目(项目储备)和相应的资金,如果地方政府也还没做好相应的准备,中央政府起码应该推出一项比较具体的一揽子财政、货币刺激计划,充分利用所谓的“宣示效应”(announcement effect),提振市场、投资者和广大公众的信心,为明年经济的较好增长表现打下基础。
【余永定:长安街读书会主讲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注:授权发布,本文已择优收录至“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北京日报、重庆日报、新华网、央视频、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视界、北京时间、澎湃政务、凤凰新闻客户端“长安街读书会”专栏同步),转载须统一注明“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出处和作者。
责编:邱诗懿;初审:陈佳妮、许雪靖;复审:李雨凡、程子茜
长安街直播
长安街读书会是在中央老同志的鼓励支持下发起成立,旨在继承总理遗志,践行全民阅读。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学习、养才、报国。现有千余位成员主要来自长安街附近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中青年干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员、全国党代表、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等喜文好书之士以及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国家高端智库负责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讲专家和中央各主要出版机构的资深出版人学者等。新时代坚持用读书讲政治,积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